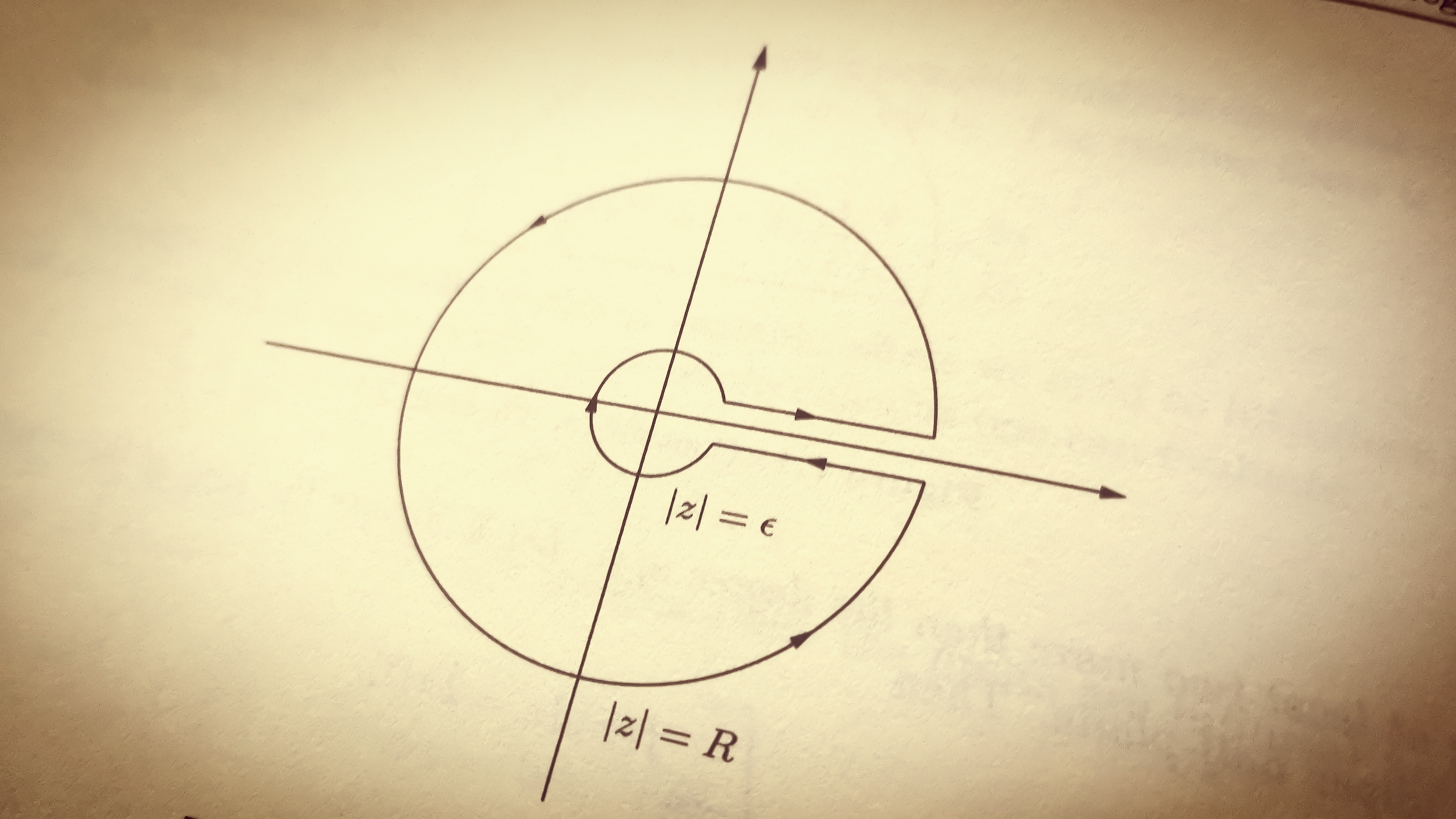忆袁隆平
 5月22日, 双星陨落,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和”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 先后逝世. 袁隆平老先生可能距离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更靠近一些, 所以今天这篇随笔, 就主要写写袁老, 以为悼念吧.
5月22日, 双星陨落,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和”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 先后逝世. 袁隆平老先生可能距离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更靠近一些, 所以今天这篇随笔, 就主要写写袁老, 以为悼念吧.
今天5月24日, 是袁隆平先生追悼会的日子. 这些天来, 关于袁老的各种新闻, 生平回忆报道, 回忆文章, 朋友圈悼念不在少数——一个人走了, 到了盖棺定论的日子了. 关于袁老的功绩, 人生, 我没有什么资格去评价, 大家都叫他”当代神农”, 我也认为这是名副其实的. 但我这段文字取名叫《忆袁隆平》, 确乎有些怪异——一者我非农学专业, 于三农亦无有什么贡献; 二者我亦不在现实生活中认识袁老, 未有交集; 三者一如大多数生活于城市之中的人一般, 不知自何年起已几乎未食过杂交水稻之粮——我忆袁隆平以何者?可起心着笔要写这文章时, 我确乎是要忆袁老的.
十里稻田, 记忆深处, 一缕稻香.
我的父亲是粮食部门的工作人员, 曾先后在军粮供应站, 基层粮管所, 储备粮库等地方陆续工作过, 而我的童年很多时候都是伴着一个个粮仓、米仓度过的. 这些粮仓每年空了又满, 满了又空, 一年两季的轮回; 粮仓外来的农人的粮车, 也一年两季的出现, 排着长龙, 首尾相接. 记忆中的粮仓, 除了少数些自然灾害的年份, 每每满起来, 似乎总是比之前的要更多, 事实也是如此——农人们谈论着新的稻种, 谈论着自己丰收增产的稻田, 还有新闻里播报的那个叫”袁隆平”的人.
那时的我, 对于杂交水稻之类的事物, 什么也不知道, 似乎也不感兴趣… 只知道, 今年的稻要比去年的多, 今年的稻和去年的一样香,今年的稻产出的米依旧饱满, 躺在粮仓的谷堆上, 双手插进刚机器去壳的热乎的米堆里, 我觉得自己是这个天下最不愁饿的人.
每每收完粮, 父亲总拿着大大的竹笤帚, 细细的扫过稻粮过称的大场子, 每一片地缝, 每一段墙根, 把粮车搬运散落的稻谷聚拢, 再用细筛,轻轻的筛去夹杂的砂石灰尘, 拾去落叶花草, 然后倒入粮仓. 我问过父亲, 我们有这么满山的粮仓, 为何还繁琐的去收拾地上这点谷粒? 父亲只是淡淡的谈起那三年的自然灾害, 谈起自己儿时的饥饿与辛苦, 他说: “天下粮仓十万, 遗谷聚粒成山.”
“不是有袁隆平吗? 你们都说他的种子很厉害啊? 这点粮食他肯定能种出来.”
“袁隆平啊? 他要是不在了呢? 你奶奶走了, 你不总念叨要吃她的青团子吗?”
“那是老爸你没学到奶奶的手艺! 哼!”
这是十六年前我和父亲的一段对话, 父亲去年也已经病逝, 奶奶的做青团的手艺也没有再被复现过. 袁老西去, 但他的杂交水稻的种子一直发展传承下来了.
长大的日子里, 也始终伴着稻花香. 老牛犁田, 我们数种子; 大人抛秧, 我们掏泥鳅; 放水引水, 我们稻花里捉鱼; 一季收成, 我们趴在打谷场的稻草堆里游戏——在中国的某一块土地上, 袁老, 也刚完成他一季的收获.
伴着亩产刷新纪录的新闻和”袁隆平”这个名字, 伴着稻花香里看丰年, 我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自己的少年, 长成了今天的青年. 大概就是如此, 潜移默化之间已然习惯了”丰收”的存在, 习惯了一个行走在陌上田间身影的存在, 他是我们那么多年敢于吃饭时常不能光盘的心理”依仗”——我自然不会浪费粮食, 却也不至如父亲一样务尽每粒稻米, 颗颗计较. 袁老一走, 我却是突然怕了, 或许我和当年父亲那样, 怕了; 或许也因为我突然明白了粮食人心里的忧思. 技术后继有人, 粮食安全却永悬颈上.
回忆的起始处, 过处, 终了, 我确乎是要忆袁老的, 我似乎忆的其实是自己的人生, 一段被”年年稻花香里看丰年”庇护的人生.
一稻济世, 万家粮足.
今天的新闻里看到一句话: “世上没有神仙, 也无需立庙, 今后的每一缕炊烟, 都是人间的怀念.” 今天起, 我要好好吃饭, 这米饭腾腾的热气, 多香啊!